象意之间,黑白之中
宇宙是一个大世界,中国书法是一个小宇宙。点画之间驰骋着广阔的哲学空间,儒之中和、释之玄妙、道之博大、同样可以从书法的章法与点画中得到体悟。
汉字是一座横跨古今的桥梁。汉字是一座挖掘不完的金矿。汉字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,其中包含着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自然、人文、艺术、哲理。
艺术,说到底就是在找“感觉”,画家在画感觉;书法家在写感觉;歌唱家在唱感觉......而我们的观众和听众,是在看感觉和听感觉。
有人讲,广釆可以博收。其实不然!如果乱釆,非但不能博收,还有可能乱了阵脚,使之原本已经形成的格调面目全非。因此,学习还是既“广博”又“约取”为好。

历史的尘埃已堆积如山,但汉字里蕴藏着的古代文明至今仍闪闪发光。汉字是人类创造的古代文明的精华,是至今仍在使用而且继续散发着光芒的文字。
寻找源流,是全面、系统、深刻认识一种书体的途径。源和流相辅相成,既要寻根求源,又要顺藤理流。
清晰源,可以帮助书家汲取创作之根之本。了解流,可以借鉴前人的方法、技巧和理念。由此前行,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。
汉字是发展联想的图画、积木,是开发智慧的魔方。
著名汉语专家告诉我们:“就储存信息量来说,点不如线,线不如面。方块形的汉字是平面文字,它比线形文字储存的信息多。”又说:“由於汉字是形、音、义大量信息浓缩成为一个个方块,独立性强,能够灵活地层层组合,因此具备了世界上其他文字所不具备的特异功能。”
中国文化精神为什么能够延续,与中国文化的继承、吐纳和自我创新有关。这是中华文化最为优秀的品质和特点。
中国式智慧的根本是:在继承中发展,又在发展中维护和保护着根本。

“力功”和“智取”应兼而有之。仅凭“力功”,则劳而少获。仅依“智取”则如无本之木,难以枝叶茂盛。学书者应二者结合,兼而取之。初学时,“力功”为主。入门后,广博约取,以融而能合者为上。
艺术的操作技巧问题, 不要太迷信理论,要靠实践摸索。手高由眼高而来, 眼高未必会手高。
眼高,是可以培养的。古人常说:“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。”是一种提高眼力的好方法,多走、多问、多看、多思考。
我们可以把“眼高手低”看作是一个过程,那还是积极的。因为“手高”肯定是由“眼高”开始的,眼不高,手怎么会高?因此,由“眼高手低”到“眼高手高”是一个过程。
师物,师造化、师自然。摹仿也,吸取也。其善者曰:能。师心,师所觉、师所悟。创新也,生发也。其佳者曰:奇。师性,师个性,任性而发,不知然而然,随其意也,随其化也。其绝者曰:神。
师物,意在物内,意在象中,则“见山是山”。师心,意在物外,意在象外,则“见山不是山”。师性,意在物内物外之间,则“见山既是山,又非山”。

吴冠中说“笔墨等于零”,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抽象地谈论笔和墨,或者是具体地谈论笔和墨,而在於笔墨如何与时俱进,与当代的文化、当代的变革挂上钩。笔者也曾说过,传统是砖瓦,前人是砖瓦,我们的任务就是取这些“砖瓦”,来盖自己的房子。
艺术作品要有自己的面貌,并非难事。自己的面貌,如能高于古人,高于今人,则难上加难。然,有志者,并不能因此而退却。
不要近亲繁殖, 要向老师的老师学习。真正的老师是几千年留下来的汉字文化, 是大自然。重复不是艺术。重复古人是自杀, 重复自己也是自杀。前人的成果, 可以营养自己。但不能拜倒在前人脚下,做古人的奴隶。要把古代碑帖当砖瓦, 学会盖自己的房子。
书法作品的成功与否,其实就是书家对空白分割的成功与否,换句话说:“就如同建筑师分割空间一样。书法家在纸上分割空间,而建筑师是在地球上分割空间。”
白与黑是相辅相成的。一张白纸因为有了黑的字,才有存在的意义。如果没有白纸,黑字也无法依存,没有了载体。
在创作中,增加笔墨易,增加空白难。一张白纸,只要写上字,白的部分会减少,黑的部分已成为现实。如何利用有限的白,创造无限的艺术境界,那是一门学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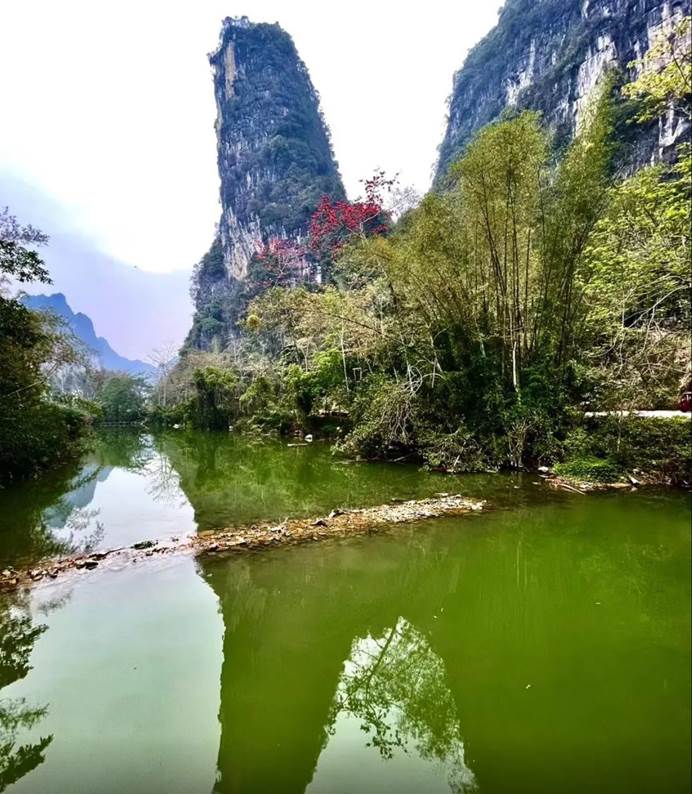
一张白纸,写上了许多字,但未觉得空白太少,黑的太挤,那就需要学会布白。“布白”,是一门学问,要学会“计白当黑”。
当我们面对一张白纸,握笔凝思,准备下笔的时候,你想到的是笔墨效果还是空白效果? 笔者以为,两者都得考虑。无空白效果的思考,就没有笔墨效果。换句话说,笔墨效果的真正涵义,应该包括布白的效果。
如果用有限的笔墨,表达无限的情感,就得学会布置空白。因为,空白的意境是无限的。空白,可以更多地赋予虚幻想象,“空白不仅是笔墨的衬托和补充,它往往是笔墨的延伸和拓展”(见蒋天耕《空白论》,载《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》)。
所谓结构,是以笔画为中心进行分布。所谓章法,则是以空白为中心,进行整体的分割。
“布白”是技巧,更是一种学问和境界。
“布白”是技巧,通过对历代名家书画作品的赏读,你就会发现,“布白”是通过改变字形结构来实现的。面对一张白纸,我们只能靠一种颜色“黑”去书写、去创作。因此,书法的主要形式,就是处理“黑白”关系。通过墨线去分割一个一 个空间,而这种空间的分割,又是通过粗细、长短、浓淡、快慢、疏密等各墨线去营造,而这么多书写的线条的营造需要技巧,不仅需要掌握各种线条的笔法,还要学会结体的方法,学会布局的方法。

可是,我们往往只关注黑,不关注白。因此,加深对“布白”的认识,显得尤为重要。
艺术与设计难舍难分。尤其在当代,艺术需要设计,设计也需要有艺术的思维与眼光。它们常常像一对孪生兄弟,伴随而行,很难区别,又必须区别。
就拿一件书法作品来说,写什么,用哪种体,写几个字,是横幅还是条幅,盖几个章,都必须有一个思量的过程。再往深处想,如何将书写的内容与你的用笔和用墨相结合,达到完美。例如,“杨柳春风”需要用较为轻快的线条和笔致来表达。而“福寿康宁”则需要用朴厚、丰实的笔趣墨韻来展现。这就需要一位书法家,具备一些如设计师一样的考量和构思。
艺术毕竟不是设计。因为艺术是在限制中寻找自由,而设计却在设计中寻找限制。
艺术思维需要自由自在的遐想,需要放飞,需要更多个性表达。所以,艺术家会日新月异,见异思迁,这样才能不断有新作问世。因此艺术的本质是揭示问题,而设计在其中只是扮演一个解决问题的角色而已。
艺术是为了探索人性,而设计只是为了满足人性的需要。
用笔千古不易”和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并不矛盾。前者是赵孟頫书论的核心,后者为石涛的名言。两位都非常重视传统的学习和继承,又都是在学习中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大家。笔者以为,前者强调了变化中的不变,而后者则侧重于不变中的变而已。
展开你的翅膀,发挥你的想象力,这是创意的前提。创意的产生让人兴奋,创意的实现让人快乐。不过你要能忍受创意实现过程的艰辛。
古人还说:“仰观宇宙,俯察品类。”意思是说,大至宇宙运行,小至万事万物,都可资学习思考,作为做学问的素材,加以思考、加以探究、加以生发。

独创性是可以培养的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养成独立观察、独立思考、独立判断的习惯,那是第一步。如果能够观察别人未观察、思考别人未思考和判断出别人未判断的事物和现象,那是第二步。
一个人有没有独创性与他的胆识有关。有胆有识,是人们形容那些既机智多谋,又奋勇大胆的成功者。我认为,有胆有识,应该换位而论,有识才有胆。
毛笔是一支慧笔”,“汉字的笔法、构成法充满智慧”,两者不谋而合。
回顾近百年汉字浴火重生的历史,看到今天汉字已经顺利进入互联网,进入现代文明的现实,我们已经有理由相信,汉字不会灭绝,古老的汉字将伴随一个古老的民族,辉煌而又自豪地走向未来。
汉字的本质是形,这是语言文字专家将人类文字分类研究得出的结果。如果从汉字书法艺术的角度出发,笔者认为:汉字的本质是象,是图。是形象,是图像,是心象。
形象也好,图像也好,心象也好,都是储存思想、认识的方法。可以这样说,中华民族把自己智慧都藏在汉字之中。每一个汉字(尤其是没有被简化的汉字)都储存着大量信息,甚至是一个故事,或一段历史......这是汉字书写,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艺术除毛笔以外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。